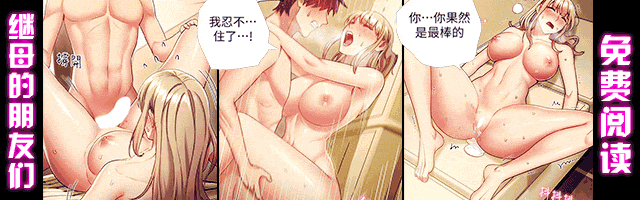四
离开酒吧街后,晚十点的人行路上宽敞安静。
伊晓垂着手,有伤,只被霈泽松松地牵着,他还在哭,这一路上就没有停下来过,哭得那撮小辫子跟着打颤儿。
霈泽想起他们的初见。
那时候也是倒春寒天将尽,伊晓穿着一件米白色的卫衣,坐在面馆外的折叠小桌上吃手擀面,眼泪砸在面汤里,哭得那么好看,叫他只瞧了一眼就动心。
他跳下单车,跑去面馆里也端了一碗面出来,在伊晓对面落座。
他握着筷子,问:“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?”
伊晓说:“我没有钱。”
这对霈泽来说根本不算个事,他道:“我给你,你要多少?”
伊晓吓坏了,连连摇头:“我不要你的钱。”
霈泽却耍起流氓,他长腿一伸,在桌下把伊晓牢牢圈住,害他连站起来都做不到。
霈泽欣赏他惊慌的模样,势在必得道:“那我包养你,意下如何?”
他们在一起整整一年,从春天初见,到春天消失不见。
又阔别两年,再重新相遇时,就是现在这副场景。
物是人非。
霈泽的指腹轻轻抚在一片创可贴上,心中一箩筐的疑问都汇成这一句物是人非。
“以前你的手上总有伤,条条道道的血痂,记得吗?”
牵在一起的手晃一晃,霈泽不知道自己在期许一个什么答案。
变成笨蛋了,那失忆了吗?
应该没有吧,不是还记着要找霈泽哥哥吗?
伊晓踩在婆娑的树影里,含着哭意喃喃:“记得。”
霈泽莞尔,倏然想要考考他:“血痂是什么?”
“是,血痂。”
“ ”
霈泽低笑一会儿,又问:“每天晚上都一个人回家么?会不会害怕?”
伊晓的另一只手还攥着他的洗碗工制服,此时被用作手帕,将自己又红又肿的小脸擦得新添好几抹脏兮兮的痕迹,狼狈得像个叫花子。
他抽噎道:“会害怕。”
能听得懂问题,只是反应太慢,也能答话,目前看只限于简单的短句。
霈泽默默叹息,仰起头看伊晓哭成花猫的脸,丑不拉几的,怪招人疼。
他说:“不许哭了。”
伊晓止不住,眼泪仍是决堤。
霈泽停下轮椅,一改之前好声哄,猛地用力一拽,揽腰抱肩,眨眼就把人捞进怀里坐大腿了。
一直跟在后面的小郑惊得头发都竖起来了,石膏刚拆没几天,哪能这么承重!
可惜不等他冲过来,霈泽就挥挥手,禁止他靠近。
夜风吹得树叶簌簌,周围静悄悄。
青石板上的影子融成了一团,伊晓吓懵了,拿一双肿眼泡看着霈泽。
“在哭什么?”霈泽凑近,用鼻尖轻轻蹭了蹭伊晓的耳朵。
“是盘子没刷完,自责的哭?还是被小刘嫌弃了,委屈的哭?”
伊晓的瞳仁漆黑水润,眼神澄澈得犹如少年。
他很慢地摇了一下头,憋着哭喘,又摇了一下头。
霈泽用鼻音疑惑,嘴唇若有似无地吻在他潮乎乎又热烫的脸颊上,他将他圈在怀里,轻飘飘真像圈了一只小猫。
有人路过,嘻嘻哈哈的高歌里突然冒出一连串起哄的口哨。
伊晓像被刺到,蜷缩的身子顿时抖起来。
霈泽将他拥紧,摁着他的脑袋埋进自己颈窝,又用手心盖住他的耳朵。
不多时,口哨声听不见了,笑闹渐远。
霈泽轻抚着伊晓的头发说起悄悄话:“晓晓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?”
伊晓不吭声。
“难道是怕我?还想躲着我?”
伊晓摇头,把发揪蹭歪了,身子也渐渐软和下来。
“那是开心的?终于找到我了?”
怀里的人又没了声,霈泽也不再追问,回过头看见小郑在树下急得直拍腿,立刻又装眼瞎,看路灯看树梢,就是不看小郑张牙舞爪地对他打手势。
半晌,轻轻一声“嘀”。
是霈泽的手表,整点就会嘀,他撸起袖口一看,十一点了。
霈泽握住伊晓的肩膀让他直起身子,发现哭包竟不知何时不哭了,只是形象过于糟糕,红鼻头红眼睛,头发乱得活似沿街流浪两个月,可怜得要命。
“睡着了?”
“唔,没睡着。”
霈泽轻轻笑起来,心道,真像个小傻子。
老小区黑灯瞎火,连一盏像样的夜灯都没有。
小郑陪伊晓上楼拿东西了,据晓晓说,没有那东西他晚上没法睡觉,执意要回来拿。
霈泽等在楼下,他抬头看这八层的老房子,别说晓晓会害怕,他都害怕。
如果住在这里的都是老人,许
是还好,若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
按照胖老板的说法,晓晓至少已经在这里住下三个月了。
三个月,每天晚上都独自摸黑回家,又是谁帮他找的这里的房子?房东知道他是笨笨呆呆的吗?或者,其实他就是和房东住在一起?
霈泽按住眉心,怕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楼梯间的触摸灯忽明忽暗,伊晓跟在小郑身后下来了,怀里抱着一个半大的鲨鱼玩偶。
霈泽记得这个玩偶,他买的,他送的,甚至连鲨鱼穿的那件白衬衫,也是他的。
霈泽发觉自己的强忍一晚的耐心终于要耗尽了。
他拉开车门,被小郑搀进座椅里,轮椅用不着他管,他倾身把呆站着的晓晓拽进车里,这才发现他背后还背着一个干瘪瘪的书包。
“包里装的什么?”
“袜子,好几双。”
霈泽只想到他穿着他的白衬衫在屋子里跑,一双脚套着蛋黄色的棉袜,衬得两条腿泼了牛奶一般。
车门“嘭”地合上,亲吻很凶地落下。
五
九棠府别墅区万籁俱寂。
凌家花园里有一张秋千椅,伊晓的目光从迈进栅栏门后就一直黏在上面,心思一览无余。
霈泽使坏,抬手对小郑道:“明天把秋千拆了。”
小郑应下。
等进了屋伊晓才反应过来,他眼神急切,微张的嘴唇不知道要如何祈求,于是又抿起,再又嘟起,看那样子倒像是在和自己生闷气。
屋里一股卤肉香。
陈婶儿迎出来,她在接到电话之后就开始忙活起来,西红柿肉酱卤子,手擀宽面片儿,万事俱备就等小少爷带人回来。
霈泽牵过伊晓:“叫陈婶儿。”
伊晓道:“陈婶儿,好。”
陈婶“哎呦”地瞧这伊晓这花猫脸,还不待应声“好”,就听一长串叽里咕噜的肚子叫,叫得她愈发心生怜爱,她催到:“先去洗洗脸,啊,洗干净了就出来吃面片儿。”
霈泽便转过轮椅,默不作声朝着客厅连廊的客房滑去,他故意的,以为会看见伊晓杵在原地傻呆呆的,没成想没呆住,竟小跑着跟过来了。
霈泽心情大好,指挥晓晓打开其中一间客房门,说:“我的卧室本来在二楼,腿瘸了,上不去,你就暂且跟我一起睡在这儿。”
伊晓谨慎又好奇地环视四周,这对他来说已经很大,墙面上有雕刻的花纹,壁灯好好看,吊灯也好好看,脚下也厚厚软软的,垂地的窗帘绣着繁复华丽的图案,随便哪一处,都比伊晓的老小区房子要精致漂亮。
伊晓问:“这是,哪里?”
霈泽想了想,说:“这是你要听话的地方---你一进这间屋子,就要听我的话,知道么?”
伊晓抱紧他的鲨鱼玩偶,小声道:“知道了。”
霈泽很满意,他滑到床边,示意旁边的衣柜道:“首先,来选一身睡衣。”
伊晓朝拉开的橱柜看去,横纵交错的木板隔断出大大小小的空间,里面或挂或叠着许多衣服,但他没动,他摸摸鲨鱼脑袋,问:“我睡在,哪里?”
睡床啊。
霈泽极轻地一咋舌,问题来了,这家伙的睡相他还是很清楚的,竖着躺下,横着醒来,床上不论放几个枕头都能给你扑棱到地上去。想当年第一次同床共枕,当晚他把晓晓干晕操醒再干晕,不打紧,第二天没做,养身子,于是晓晓恢复些精力,一晚上把霈泽闹的,抱着都没用。
简言之,睡相奇差。
霈泽看向自己尚未痊愈的左小腿,放弃的念头油然而生。
再者,今晚在车上强吻晓晓,还把人给吻生气了,好不容易歇下去的眼泪卷土重来,哭得霈泽头大,索性又按在怀里亲了一通,以毒攻毒,竟奏效了。
小傻子的心思你别猜。
霈泽把选择权交给伊晓:“床,沙发,你选吧。”
选床的话,他就想想办法,选沙发的话,他就再抱一床地毯来垫在沙发下头,滚下来也摔不疼他。
伊晓朝云团一样的大床看去,太大了,没有安全感,空荡荡的。
他朝沙发走去,有靠背,可以把后背紧紧贴在上面,后面被兜着,前面抱着鲨鱼,这样才能安睡。
伊晓把他的鲨鱼先生挤在角落里,挨着鼓囊囊的靠枕,他嘟囔了一句什么,声太小,霈泽没有听见。
“我,好了。”伊晓走回霈泽身前,按照指令选了挂在最外面的一身深蓝色睡衣,触感绵软,他一拿在手里就很喜欢,他奋力思考,这让他本就红肿的脸蛋烧得更加热烫,“我,要穿吗?”
“当然要。”霈泽笑起来,怀里不知什么时候抱着一个小药箱,“全都脱了,脱光,再穿上它们。”
还以为会吃惊、会害羞,至少会扭捏,却不想晓晓只迟钝地听明白意思后,就抱着睡衣回到沙发前,先脱下棉服,叠叠好
,四处瞧瞧,最后决定放在沙发脚旁边。
霈泽隔着大床看他,像在欣赏一出默剧。
晓晓弯下腰,脱去他有点肥的牛仔裤,里面竟然什么都没穿,直接露出两条笔直又匀称的腿。
霈泽皱起眉,天还冷,他都还穿着秋裤,这小傻子是心大还是真的不会照顾自己?
那圆圆翘翘的屁股蛋该是身上最有肉的地方了,就被一条白内裤和牛仔裤罩着,以这点儿装备往地上摔个四仰八叉,是不是得摔青了?
白内裤也从脚踝滑下去了,连同一双白袜子一起放到地上去,只剩一件宽松的针织衫了,不新不旧,随着被揪住领口脱去而微微变形,再遮不住那段纤细的腰肢和单薄的肩背,最后也被搭在沙发上叠叠好,摞在了沙发脚旁。
霈泽眼神沉沉,望着这具白皙的背影心跳加速,连呼吸,也有一种干柴烈火般的灼热。
太多酣畅淋漓的画面在脑海里汹涌起伏,那段腰肢他握过,柔软柔韧,会拱会扭,那两枚小巧的腰窝也会在它们主人情动时盛满勾人施虐的情欲,伴着一声声“哥哥”而抵达高潮,颤得像要被揉碎了。
他还记得么?记得这些春宵和纵情么?
霈泽看着晓晓提上他穿过的睡裤,大了起码两个码,直往下掉,弯腰提了三回还是一松手就光溜溜,可怜可爱的,会怎么办呢?
霈泽抿起笑,看他垂着脑袋沉思片刻,不来第四回了,而是改去穿睡衣,埋头系扣系半天,这才拎起裤头转过身,打着赤脚,敞着一大片锁骨肩头回来领命。
还是那句话,伊晓顶着一张通红的小脸道:“我,好了。”
霈泽心道,我不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