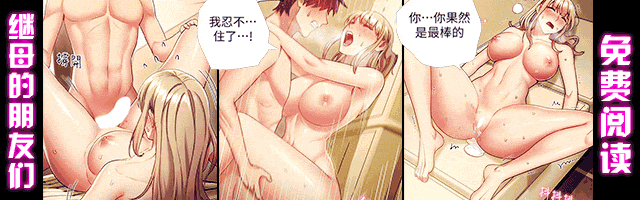飞驰的马车中,霍忠尧枕在叶雪舟的膝上,听他讲述了这半年多时间里,他与斛律飞的经历。
话说当初斛律飞与叶雪舟打定了主意,打算一边收留路上的流民,一边寻找安身之处。此后,他们一路往东,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跋山涉水,终于找到一块水草丰美却又人迹难行之处。
若要说有什么地方既能遗世独立,又能让人安居乐业,那自然是地势险要的溪谷或者山顶平原之地。而龙骧山正是这样一块理想中的桃源乡。
当时,跟随斛律飞的流民已经数百人,其中有汉人,也有胡人,最难能可贵的是,这些人竟大多都能相安无事,也愿意跟着斛律飞一起白手起家。
大家一致决定,就在此处安顿下来,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埋头苦干。一众人堆石布土,筑起亭障,在龙骧山上建起了一座坞堡。斛律飞率领着一众乡亲们在坞堡周围开垦荒地,引水耕牧。
与此同时,斛律飞还在不断接纳前来投奔龙骧坞的闾里乡亲。人多力量大,转眼间座座垒壁平地而起,阡陌纵横交错,这一小块巴掌大的地方,竟也被他们经营得风生水起,有声有色。
他们把新的家园称作龙骧坞。
如今,当初小小的据点如今已是近万人的聚落,光是斛律飞手下的部曲就足足有数千人。
霍忠尧躺在叶雪舟怀里,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地听着,心中感慨万千。
这是霍忠尧有生以来最为煎熬、最大起大落的时刻。曾经那样相信的人说背叛就背叛,曾经一度被质疑是养虎为患的人却救自己于危难之中。人生就是这样处处充满了意外,盛极必衰,否极泰来。
霍忠尧来到龙骧山时,时间已是翌日清晨。
沿着一条林荫道,穿过山脚的城门,霍忠尧就算是踏入了龙骧坞的地界。整个坞堡依山而建,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道盘旋而上,各种屋舍星星点点地错落分布于绿意盎然的密林之间。
霍忠尧来不及欣赏景色,就被送到了斛律飞所说的山顶小屋。
斛律飞迅速地把整个坞堡里的大夫都召集过来,为霍忠尧看诊疗伤。霍忠尧趴在榻上,正在接受针灸将体内的残毒逼出之时,霍衍之与刘氏出现在了门口。
“爹!娘!?你们怎么也在这儿??”
霍忠尧诧异地睁大了眼睛,刚要起身,骨头便一阵咯咯作响,疼得让他倒吸一口冷气,霍衍之连忙上前将他的身子按下:“稍安勿躁,我们已经来了好几天了。”
“是叶公子将我们一家接过来的。”刘氏在一旁补充了一句。
霍忠尧本来还有点担心淮陵王会不会对他的家人不利,直到霍衍之向他讲述了这些天的经历才知道,原来在他入狱之后,得知消息的叶雪舟就抢先一步派人将霍家人全都接到了龙骧山上来。
夫妻俩在儿子入狱后就立刻离开了建康,因此这也是两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审视儿子的伤势。在看到霍忠尧背上那触目惊心的伤痕时,一向硬气的刘氏也忍不住掩泪。
“你说咱们霍家一向小心翼翼地,怎么偏偏尽招些小人。真是造孽!”
“娘,别哭了,孩儿这不是生龙活虎的嘛。”
“是啊。”霍衍之感慨地叹了口气,“为父本也以为这一次咱们霍家是在劫难逃了,没想到,天无绝人之路。”
说到此处,霍衍之冲着一旁的斛律飞深深鞠了一躬。
斛律飞赶紧将霍衍之搀扶起身:“老爷这是做什么?”
霍衍之紧紧地握着斛律飞的手:“斛律公子,平心而论,当初你到咱们霍家来,咱们有眼无珠,大大地亏待了你。可如今你却不计前嫌,不惜以身犯险救出我儿性命,还护佑我们一家平安,这份大恩大德,老夫实在是不知该如何报答才好。”
霍忠尧听到此处,忽然心中一动。他四下张望,发现似乎没看到霍云生的身影。
“霍云生那臭小子呢?怎么没见到他人?”霍忠尧道。
“我叫了,可倒霉孩子怎么都不肯来。”刘氏一提到霍云生就气得把脸拉得老长。
霍忠尧倒是丝毫不意外,只是忍不住苦笑,霍云生还是那个霍云生。
“其实你也别怪那孩子,他就是脸皮薄。”霍衍之怕霍忠尧被气伤身子,接过话头安慰道。
“无所谓了。”霍忠尧望着头顶,长长地舒了一口气,“只要大家都还好好的,就比什么都好。”
是的,这一场飞来横祸的确是让霍家失去了在建康的家业,但是俗话说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经历一场大难,一家人能够全须全尾地在龙骧坞团聚,就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。除此之外,霍忠尧也没有其他什么奢望了。
太阳落山时,看望霍忠尧的众人纷纷散去,入夜后,小屋里便只剩下了斛律飞与霍忠尧。斛律飞用叶雪舟亲手调制的跌打药油,替霍忠尧涂抹在身上。尽管霍忠尧背后的伤口已经基本上结了痂,但斛律飞的动作依然很轻,像是在触碰什么易碎物一样,一举一动小心翼翼。
霍忠尧双臂交叠地枕着下巴
,趴在床上,虽然后脑勺没长眼睛,看不到斛律飞的表情,但能感觉到有一股炽热的气息,一下又一下地扑在自己后颈上。
“会疼吗?将军?”
“还好。”
“那……这样舒服吗?”
斛律飞不厌其烦地在霍忠尧耳边呢喃,弄得霍忠尧心里火急火燎的,说不出的痒。
“什么舒服不舒服,”霍忠尧嗤地一声低低地笑了出来,“你这话问的好生奇怪。”
“我怕将军还生我的气。”斛律飞黯然道。
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斛律飞一句话,勾起了两人之间那段有些不愉快的回忆。
“笨狗,”霍忠尧故意将眉梢一挑,“这么记仇啊?”
霍忠尧记得自己当时气坏了,可是现在,自己似乎一点也不抗拒与斛律飞的肌肤相亲,用一句不太恰当的话来做比喻,这或许就叫小别胜新婚吧——虽然他与斛律飞不是夫妻。
斛律飞见霍忠尧不说话,心里有些忐忑,生怕自己又说错了什么,讪讪地闭上了嘴巴。
“那件事,早就过去了。”霍忠尧翻了个身,直视着斛律飞的眼睛道。
斛律飞一怔:“真的?”
“当然。”霍忠尧长舒一口气,眼角温柔地下垂。
斛律飞两眼倏地绽放出光彩,一声欢呼,猛地拥住了眼前之人。霍忠尧稍稍有些吃痛,却不挣扎,而是任由他抱着,然后伸手环住对方的背。
“我等了九个月又十六天,”斛律飞把头埋在霍忠尧肩头,瓮声瓮气地道,“终于等到了将军这句话。”
霍忠尧忍俊不禁:“不愧是我的小笨狗,记性可真好。”
“将军,我好想你。”斛律飞抬起头来,有点小委屈,“将军呢?你想我吗?”
霍忠尧一怔,沉默了。